编者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发展的必然,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赵智奎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种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四个部分,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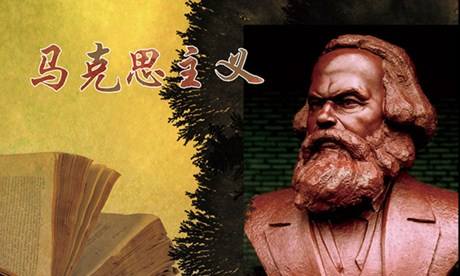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赵智奎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研究
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世界上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逐渐减少。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的气数已尽,21世纪将建立一个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的世界秩序。他们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是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的社会舆论。
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宣称正相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而且随着马克思本人被评为“千年伟人”,呈现出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主义仍在世界的大地上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而且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当西方政客看到中国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这样一个事实,就不得不感叹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在世界上仍然高高飘扬,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正如当年西方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时,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教条,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只能中国化,必须中国化,必然中国化,舍此无他。具体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和“具体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至于论文,也是数不胜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因而相关成果非常丰富。比如:丁守和等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年版);林代昭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茂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高军等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柳国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德旺的《新编五四运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程恩富等的《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梅荣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庄前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学者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美国学者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一批汉学家对于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成果显著,其间有多处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另外,韩国学者宋荣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多有论述,说“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面发表了很多著作。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美国作家罗伯特·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熊玠的《习近平时代》。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和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时代的产物。这一伟大学说一经创立,就很快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所以,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坦陈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如,列宁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邓小平同志写的《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述了他从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间的重要著作119篇,其中73篇都是同国外政要或其他来宾的谈话,占全部篇目的61%。诸如“小康社会”“翻两番”“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观点,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首次公开阐述或详细介绍的。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对外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全人类性的科学真理体系,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和发展自己的行动指南,是世界性的理论,必然要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和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必然性,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阶级性、时代性、科学真理性以及人民大众性的理论品格,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欧洲化、俄国化的进程,其时代化、大众化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共同演绎了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20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阐述这个历史进程,我们以1880年春夏之交,恩格斯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例。这是一篇历史文献,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著作一样,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欧洲化和俄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要求。把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连在一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品格。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需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种主观意愿,而是实践的呼唤和需要。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理论内容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中国化、世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是指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已传遍欧洲并被付诸实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在恩格斯那个年代,就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恩格斯这样说,1880年法文版的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上述情况表明,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是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成果。此后,进入20世纪还有一个俄国化问题——列宁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也包括俄国化。
综上,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俄国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不同历史阶段,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则是一个历史总趋势。无论是欧洲化、俄国化还是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区、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其 “民族化”“具体化”,这才是“化”的要义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入中国,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同学》中提到了“马克思”,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的马克思的中译名。但这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译著。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首次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9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把麦喀士(即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之泰斗”。
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1905年,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和中心思想,并节译了其中的十项纲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是陈望道于1920年翻译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留沾粽子。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这个故事,以党史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广大干部保持理想,坚守信仰。
《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全译本是吴黎平在1930年译成,但是他的劳动结果出版之后,这位译者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费了十年工夫。郭大力和王亚南于1928年开始翻译,第一卷译稿尚未问世,就在1932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炮火烧毁。1934年两位译者又再次从头开始翻译,一直到1938年,才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印制出版。
第二,马克思主义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到日本留学?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强国,吸引了许多中国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的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十月革命后,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到中国。1919年1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在当时中国颇为流行。“社会主义”一词也是在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
李大钊同志于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并于1916年5月回国。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的时候,李大钊同志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留日期间,李大钊同志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9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另外,“三李”中的李达曾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从法国、德国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许多都有旅欧经历。五四运动后,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赵世炎、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罗亦农、彭述之、向警予、朱德、蔡畅、聂荣臻、李维汉、李富春等赴法国勤工俭学。
比如,蔡和森。他1895年3月出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在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先后致信毛泽东等,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要发展中国革命,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周恩来等人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接受了有关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不限于法国,而且包括德国和比利时。周恩来曾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往往较长。在柏林,他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十二岁的朱德。朱德后来通过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四,列宁主义从苏联传入中国。列宁的著作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的。1919年9月,北京《解放与改造》杂志刊载了列宁在1917年写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这是我国报刊上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
此后,我国先进分子相继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团体,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开展活动的初期,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亲自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的任务是:秘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翻译著述。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在全国建立了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特别是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尽管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仍然出版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宁论游击战争》等著作。
1921年,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赴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先后有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到1927年上半年,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人员前后达百人以上。至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叶挺、王稼祥、秦邦宪、王明、俞秀松、朱瑞、左权、乌兰夫、杨尚昆、陈赓、伍修权、张如心、陈伯达、刘伯承、凯丰等。
1921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首先由团转党,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接着又组成了中共旅莫支部。1922年初,任弼时、肖劲光等先后也由团转党。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由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组成。可见,这些早期留苏的我们党的先驱代表人物成为后来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上述三条渠道传入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也就是如何“化”的;而“化”出来了什么,则是“化”的结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时空上“化”的进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民族化”“具体化”而“化”出来的结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成果,是诞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脉络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而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过“民族化”“具体化”而“化”出来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并且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可见,在本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其理论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实践形态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其制度形态即社会主义制度和未来共产主义制度。从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可称为原生理论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一原生形态和其衍生形态上发展而来的新的理论形态。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且与科学社会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理论,并没有实践。直到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开始了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原生形态,之后的列宁在这一原生形态上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创立列宁主义,形成原生形态的衍生形态。那么,中国呢?科学社会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其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比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与俄国的中心城市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并不一样。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上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如,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新的诠释和发展。
我们说,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上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推进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制度,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体系化、形态化,是其逻辑进程的必然。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从两次历史性飞跃来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推进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至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始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展开,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制度,特别是党的制度建设,在当前显得尤为突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并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退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这就是从制度形态上来讲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具体的形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的统一。也就是说,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指的是对外传播。那么,为什么要“走出去”?这是一种必然。
从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俄国化、中国化进程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西方所谓的“革命输出”,因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吸引了很多国家来取经、学习。这就是一种需要。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也就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版本。比如,从过去的经济特区到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行示范区建设,这一成功发展经验引起国外广泛关注。当然,这些思想和实践不能照搬照抄,只有结合各国具体实际才能取得成效。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大贡献。比如,袁隆平的水稻研究可以帮助世界很多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再比如:中国的高铁技术走向世界;中欧班列为欧亚大陆打通国际贸易“大动脉”;“一带一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就自然体现出来了。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一直“唱衰中国”,不断叫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妄图遏制中国发展。但结果呢?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此,“中共学”在国际社会上成为显学,各国学者对此展开深入研究。这也是一种必然。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要“走出去”。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的国际关系,要拥抱新时代、认清使命不掉队,走在时代前列,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因为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要更好地适应“两个需要”(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和“两个走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就要加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对外宣传。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上,要注意五个“紧密结合”:一是要与国家总体外交紧密结合;二是要与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紧密结合;三是要与宣传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紧密结合;四是要与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紧密结合;五是要与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紧密结合。同时,还要注意话语体系建设,提炼出在世界上有独特影响力的中国式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就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政策、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创新和全面推进的系统工程。具体来看:
第一,当前,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变,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第三,各国政党相互借鉴治党治国经验,共同提高执政和参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是开放包容的,既向世界介绍我们的经验做法,也向世界学习。
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需要加强交流、增进理解。2000年,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了越南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所,看到该所出版的杂志英文目录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翻译成“China-coloured socialism”,直译过来就是中国有色彩的社会主义。当时,我就指出这个翻译错误,并进行了纠正。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翻译成“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在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别”。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才有了中国特色。由此可见,“China-coloured socialism”这一翻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非常肤浅。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对外交流。要注重这方面的宣传。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翻译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一系列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在2017年,联合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了多项决议之中。可见,“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面旗帜。然而,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名片,这一高频术语曾一度遇到翻译问题。
以党的十九大为节点。之前,外交部、China Daily、新华网、中国网、人民网、《北京周报》等官方网站对“命运共同体”主要有三种译法:
第一种,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第二种,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第三种,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其中,第一种译法在国内外使用的最为普遍,但第三种译法“shared future”最能准确表达“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内涵。《现代汉语词典》中“命运”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生死、贫穷和一切遭遇,如悲惨的命运;二是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如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显然,“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指的是后者。所以,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是最准确、最合适的译法,并最终在党的十九大文件中正式确认下来。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的必然性,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因此,要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就要学会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之治。
|
|
||||||

 苏公网安备 32102302010175号
苏公网安备 32102302010175号